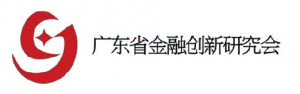【深居广东西部一个小县城里的养猪养鸡企业,为什么能成为创业板乃至整个深市市值最大的“巨无霸”?创始人早年留下的“企业性格”、全员持股制度以及对技术进步的重视,成就了它的财富神话。但现在,它遭遇了新的问题,包括环保红线、土地瓶颈等。】
“没什么变化呀?要说感觉,就是又被你们打扰了。”
2015年11月10日下午,48岁的黄植强一边为南方周末记者倒茶,一边操着“粤式普通话”开玩笑。
就在一周前,他的“合作伙伴”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温氏股份”)通过换股吸收合并方式登陆创业板,上市当天流动市值超过2000亿元,一举成为创业板乃至整个深市市值规模最大的“龙头企业”。
一时间,温氏财富神话引起议论纷纷,许多人质疑为资本泡沫。
不过,外界并不熟悉的温氏股份,在行业里却早有声名:2005-2014年10年间,温氏年复合增长率20%,利润增速21.47%,成为国内最大的畜牧企业。2014年公司营业收入380亿元,净利润26亿多元,销售肉鸡近7亿只,占全国销售总额近1/10,肉猪销售1200多万头,生产量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
抛开估值等资本市场因素,一家深居广东西部一个叫新兴的小县城里的养鸡养猪企业,为什么能成为这样一个“巨无霸”?
相比起温氏上市引发的市场喧嚣,老黄更关心自己猪栏里的现实:他身后的电视屏幕里没有播电视节目,而是分格显示着不同的监控画面——十余个监控摄像头扫视着他的六十余亩猪舍和鱼塘。全自动的投料和刮粪清扫、温湿度调节养殖系统,让他在房间里“轻松养猪”。
早在1998年便开始以“公司+农户”形式与温氏合作养猪的黄植强,养殖规模从17年前的数十头增长到今年的1800头,并在2012年成为温氏集团的首家“物联网自动化养殖示范户”。
自此之后,黄植强最主要的工作反而成了“接待参观”: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的参观者们,好奇地打量着“物联网猪舍”内的每一个细节,反反复复地问着相似的问题——养了十几年猪的老黄现在觉得“这活儿比养猪还累”。
1990年代,黄植强是新兴县城里为数不多的西饼店“面包师傅”,但他的小店没有顶过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而倒闭,思前想后之下,他最终包了60亩土地养猪养鱼,并成为温氏的农户。
此时,温氏已经养了十几年鸡,在当地越来越有名气。
已故的温氏创始人温北英,1932年出生于新兴县一个书香世家,早年的坎坷经历和自身佛儒综杂的学理思想,使其在青年时期便形成了兼具儒家社会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大同主义”价值观。1983年,身为新兴县食品公司干部的温北英停薪留职,联合七户八人集资8000元创办的簕竹鸡场,也因此带上某种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所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式的理想色彩。
在当地人的讲述中,温北英在1986年为了帮助经营砖窑生意失败的村民何凤林改行养鸡,针对其缺乏经验和技术的状况,提出“养户记账领鸡苗和物料,公司统一收购代销”的办法,其后成为温氏发展壮大的里程碑,“公司+农户”的商业模式就此延续下去。
在这个模式中,不能不提的一项重要制度,便是全员持股。
这也是温氏“同创(业)共富(裕)”的企业经营理念与“文化基因”的早期标志:1990年温氏养鸡产业初具规模后,推行“全员持股”制度,发展了几千名股东——这一与华为近乎同时推出的全员持股机制一直延续至今,早期入股的员工如今大多身家千万甚至上亿。
据温氏股份上市报告显示,在公司上市前夕,现任董事长温鹏程所持股份不足5%,11名温氏家族成员所持股份比例仅为16.74%——由于员工股东人数超过了“公司发起股东不得超过200人”的法规限制,温氏集团在等待近十年之后,才依照新政策以首家“非上市公众公司”的身份通过上市审批。
承载着创始人理想的员工持股机制不仅增强了企业凝聚力,更在此后遭遇行业性巨灾时成为共度难关的精神纽带。
上世纪90年代新兴养鸡业曾经历过一段“年年倍增”的高速发展阶段,并在1990年代中期形成了号称“三温一古”的四大养殖场格局。温氏仅为其中之一,与其他三家规模相当。
1997年全国性禽流感爆发,养鸡行业陷入“灭顶之灾”:肉鸡销量暴跌的同时,价格从每斤五六元暴跌至一两元。几乎同时爆发的亚洲金融风暴,引发信贷紧缩,更加剧了企业的现金流压力。
“三温一古”中的另外三家就此分别退出。而温氏凭着其全员持股机制下的“同舟共济”,与前期稳健经营所建立的风险基金,不但继续履约收鸡,而且还保证农户能有盈利。
“当时公司基本上是收一只亏一只,但农民还有赚,只是赚多赚少而已。”一位1990年代初便关注温氏的当地县畜牧部门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发挥了关键作用,“农民都是眼看口传的,看见跟温氏合作能赚钱,自然就去了”。
经此一役,温氏于1998年反而扩张,正式跨入养猪行业。包括这位负责人的亲戚和黄植强在内的诸多养殖户们,都是冲着“跟温氏能赚钱”的口碑,跨入了他们此前从未接触过的生猪养殖领域。
此后,公司与农户的合作模式,也不断在变化:先是“义务帮忙”,帮周边农户代买鸡苗饲料,顺便帮他们收购肉鸡销售;随着公司自身的种苗场和饲料厂陆续建立,“代买代销”模式便渐渐变成了产业链分工——温氏负责投资大、技术性强和市场风险较高的育苗、饲料、防疫以及市场销售等环节,农户们则渐渐集中到养殖环节,最终形成了市场研究机构们所观察到的“养殖服务企业”模式。
一位温氏员工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了现在的模式:农户建好场地之后,就去温氏领猪苗和饲料、疫苗等,“记好账,不用给钱,光给每头一两百块左右的押金。”每一户温氏都会派技术员跟踪,一个技术员大概管三五十户,养到5个月200多斤左右,“技术员就告诉他明天或者后天这个猪要怎么出栏,就带买猪的人直接去他那里”。
这一被研究机构总结的“轻资产、高回报”的“公司+农户”模式,在过去二十多年中被无数同行学习和模仿,但总是被形容为“看得见、学不会”。
在温氏工作了十余年的温氏股份董事会秘书梅锦方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在他看来这些研究者们都忽略了一个关键背景,“其实温氏的商业模式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在二十多年发展过程中自然生长起来的。从先董事长到现任管理层都非常注意各方劳动者的利益平衡。”
在梅锦方看来,“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下,农户还是属于弱势群体,“你不去考虑他的利益,他也不会跟你长期合作下去”。
“生意人每一单生意都要赚钱,但企业家会认为,今年亏了明年我还能赚回来,重要的是大家一起把事业做大。”梅锦方表示,这种思维方式已经不是“商业计算”,而是近乎某种“企业性格”。
“温氏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技术进步”,前述畜牧部门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1992年他们曾请来华南农业大学两位教授为新兴县养殖企业讲课,最后两位教授一直跟温氏合作到退休。
当时,温北英就以10%的技术股权形式邀请华南农业大学与公司全面技术合作,后来渐渐发展到“产学研一体化”基地模式。
南方周末记者在“中国知网”网络数据库中的检索显示,以华南农业大学为发表单位的温氏集团论文便达六百多篇,涉及疫病防治、养殖技术到经营管理乃至三农政策等诸多领域。现任公司副董事长的温志芬亦兼任华南农大客座教授,并发表了多篇专业论文。
这在养殖企业中并不多见。不仅帮助温氏在养殖技术上进步,而且在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和发展视野上也与传统的“乡镇企业”有了明显不同:早在1990年代初温氏便在华南农大的技术支持下,开始了自建局域网式的“信息化管理”尝试;到了2005年,经营规模已经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温氏,在企业管理软件巨头金蝶配合下,建立起“量身订制”的集中式信息系统(EAS系统)与集团运营决策支持数据平台。
这一系统不但能及时反馈全国各个区域市场销售状况和经营数据,而且还能直接观察到养殖户联网猪舍每一头猪的养殖数据。
在温氏“起家之地”簕竹镇石头冲村,“自动化养鸡示范户”温志开的妻子向南方周末记者展示,2012年前他们两夫妻一起能养六七千只鸡,而她现在一个人管着三个大棚里的18000只鸡。
骑着摩托刚从山上回来的温志开则告诉记者,空下来的他在2013年又包了几十亩林地种桉树,“两年后就能砍了,到时看看能赚多少。”
这种自动化改造,大大解放了农户的生产力。养猪户黄植强的一栋自动化猪舍可养猪1000头,只需他一人管理;而另外两栋尚未完成改造的传统猪舍,一共只能养800头猪,还需要另外请两名工人。
前述畜牧部门负责人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新兴县现有八千余户养鸡户,多年以来平均养鸡规模在六七千只,“孩子们都出去打工了,两个人在家也只能养这么多”。但是随着自动化养鸡技术的推出和不断完善,近两年养鸡规模达到3万-5万只的“大户”已经有两三百户了。
“前两年温氏给我一个数据我不信,打电话到养户家问他养了多少只鸡。”该人士说,他看到的数据是3万只,但到打电话时才发现“人家已经养到5万只了”。
“养鸡和养猪都是周期性很强的行业,你可以适应周期但不能回避周期,”梅锦方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像2013年和2014年就是“鸡周期”和“猪周期”共同的低谷,对企业利润影响很大。对此温氏通过这些信息平台所作的前期信息搜集分析,一方面控制规模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则利用多元化金融工具进行投资套保以减少损失,“前两年我们养殖业收益才两三亿元,但投资收益也搞了几个亿,对利润下滑有个缓冲作用”。
与此同时,温氏对养殖户们的收购价格仍然稳定上涨。“涨幅也许不太大,但是能保证你劳有所得。”梅锦方表示。某种意义上,庞大的温氏集团就象市场波动的“缓冲器”与“安全垫”。
“既然规模化养殖已经成为关键,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中小规模的散养户?”
面对南方周末记者的这个问题,梅锦方沉吟片刻:“不好找地”。
这是温氏面对的新问题。
随着近年农村土地功能调整和流转增加,养殖大户们不时发现自己看上的地因为是基本农田而没法承包。
同时,随着各级政府对环保的重视,许多地区划定了严格的“限养区”和“禁养区”,养殖规模也难以扩大。
“2000年前你来新兴,一进城就闻到满街的鸡猪屎味”,前述畜牧部门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因为当时没有相应环保政策,许多有机肥加工厂把收来的粪便堆在街道旁晾干,“连新兴本地人也受不了”。
但现在,“满城粪味”在新兴已成历史,近两年又成立了新兴江环境治理办公室,“把沿江附近的养殖场都清理了”。
环境治理的效果有目共睹,但对于农户们而言,“环保指标”却成了他们扩大养殖规模“政策红线”。
养猪大户为黄植强为南方周末记者算了一笔账,算下来是一户养500头猪(一年两栏1000头)还不如出门打工划算,因此散养户近年逐渐出现“弃养”现象。
他指着自家猪场旁边一片抛荒的耕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没法包下来,是因为“没有指标”——这个指标,是指政府根据猪场的粪便污水处理能力,为猪场设定的“养殖上限”,要提高养殖数量,就必须相应提高环保排污处理能力。
黄植强说,猪粪可以通过固液分离机干燥后作为有机肥或鱼饲料,比较难处理的是猪尿和污水——必须在净化池中通过水浮莲等植物分解后,再排入鱼塘进行二次“生物净化”,此后才能排入沟渠,“直接排放是要罚款甚至关场的”。
但对温氏股份而言,“环保红线”并非仅仅意味着成本与风险。
梅锦方坦承,由于畜牧业的环保概念刚提出不久,公司在这方面“找不到什么现成的经验和技术”,只能自己摸索创新,比如联合技术研究部门对各种地理和气候环境下的环保模式进行专项研究,设计出符合不同区域特质的环保技术体系和实施标准。
就在黄植强的养猪场旁,南方周末记者看到一个桶状的设备。“那是温氏在这里测试的净化装置”,黄植强说,公司技术员已经来“搞了好几个月”,现在的净化效果还不太理想。
“你看外边玻璃管里的水还是黑的,什么时候能变成透明的,就表示这个水可以直接排放了。”黄植强听说,温氏最近在韩国找了一家技术公司合作,“过几天可能韩国公司的技术员也会来这里”。
来源 | 南方周末